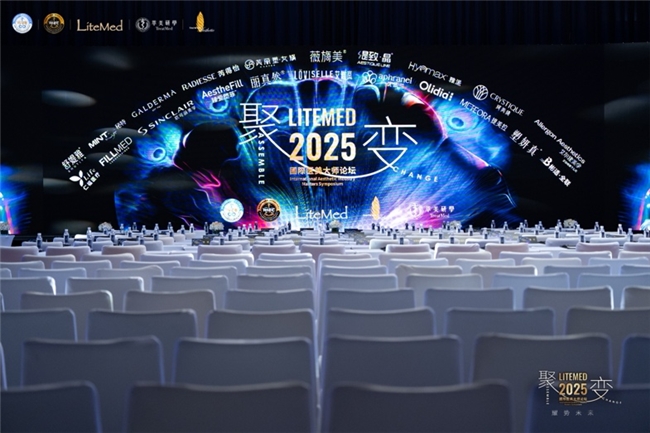张耀东
作为一条商业的和文明的通道,不管有多么险阻,它首要有必要是一条能够保持根本生命的通道。瓦罕走廊从它的地舆特征中不难找到其逻辑性。但很惋惜,关于它的大半程,咱们无法如马可·波罗、玄奘或奥莱尔·斯坦因那样亲自用脚步去测量,而只能经过地图去抽象地演绎。好在,咱们总算获得了体会一个阶段的时机。
数次前往我国最西部的小县塔什库尔干,并数度从科克牙尔沿塔什库尔干河一路走到红其拉甫,对那里的冰峰、雪岭、冰川、达坂、溪水、草滩、羊群、牦牛、营房、城堡、筑垒、军台,以及那里的塔吉克人,或多或少现已有些了解,但却唯有两个当地一向归于空白。其一,是广袤的塔什库尔干南部天然保护区,其二,是穿越帕米尔天界的瓦罕走廊。
这次进入塔县,我建议同行者放弃俗人必往的金草滩,而另走高山草场,去寻觅不同的视点,而所去草场,恰是瓦罕走廊我国段的极西部位。由此,便成果了一次瓦罕走廊我国段之行。
瓦罕走廊我国段东起塔什库尔干县达布达尔乡排依克,西至阿富汗国巴达赫尚省东部边境,全长约70公里。自阿富汗国巴达赫尚省东部边境以西,是瓦罕走廊的阿富汗段,全长约230公里。这条总长度约300公里的走廊,居然以其妖娆颀长的身段,穿越了撒拉阔雷岭、喀喇昆仑山、穆斯塔格山与兴都库什山的交混地带,东西凿穿挺拔的帕米尔天界,构成一条细长的、连通华夏文明、印度文明、中亚文明、波文雅明和欧洲文明的高原通道,为比如梵学学者玄奘、法显、慧超,地舆探险家马可·波罗、文雅·赫定、奥利尔·斯坦因,唐朝名将高仙芝等前史名人,以及千年来的丝路商旅供给了演绎人类文明的舞台。
这都是些尽人皆知的材料。但在一个旅行者眼中,瓦罕走廊的实在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?这种猎奇,曾令我像一个酒徒,在每次路过这个幽幽静“巷”的巷口时,都会因为巴望闻到深巷内那种奥秘的酒香而犯心思。可是这次,咱们却真的要走进它。
不缺水的干旱高原
2013年8月初,正是国人纷繁喊热的时节。抵达海拔3200米的塔什库尔干县城,午后的气温竟也高达32摄氏度。咱们就是在这种酷热中向南进发的。当咱们挤进一辆银白色帕杰罗向南行进不久,拍摄家包迪教师就被逼褪去了他的保暖线裤。那是他根据多年的经历,在动身前特意穿上,以抵挡帕米尔高原上凌厉的北风——这次,他失算了。
从河水的流量,也能够推测出气候炎热的程度。国道314西侧那条比素日广大多了的河道,因为零温线的上升,迫使更多的冰雪融化为水流,沿塔什库尔干河汹涌北去。而咱们刚好逆水而上,前往兴都库什山下,去那个“一鸡鸣三国”的当地。
瓦罕走廊周围都是些挺拔的、多冰川的山脉,这必定决议了依山而生的塔什库尔干河是一条多枝杈的河流。东自我国,南自巴基斯坦,西自阿富汗,北自塔吉克斯坦,很多的水流纷繁汇向这个洼陷的河谷地带,这就使得这儿成为一处虽然年降雨量只要68毫米,却并不缺水的“干旱高原”。
假如不是被一种前史知道所推翻,这种“不缺水的干旱感”简直会随同咱们的全程。从动身伊始,银缎似的塔什库尔干河就一向与咱们形影相随。100公里今后,当咱们向西折入走廊今后,塔什库尔干河的首要支流喀拉其库尔河又来陪同咱们。在前往中、阿鸿沟瓦基里的90公里路段上,南北两边的每一条山峡简直都有一条吼怒的山溪汇入喀拉其库尔河,更不用说那些散布在草滩上的小溪和清泉。这就使得咱们的视觉在全旅程中都没脱离过水。但,地表水的丰盈却于大气湿度无补。一路上,咱们须不时地抓过矿泉水瓶,去润泽那总觉得有些焦干的嗓子。
这种“不缺水的干旱感”,在走廊的东端峡口部位却被转换为一种崇高和庄重。那里是喀拉其库尔河与敦巴什河的交汇处,也是萨拉阔雷岭与喀喇昆仑山的联接部位。在这片广大的,由昆仑山、喀喇昆仑山与萨拉阔雷岭护卫着的三角地带,一片杰出的台地高悬在塔什库尔干河的东岸,与瓦罕走廊那个盅形的进口遥遥相对。在台地的西侧边沿,一字摆放着大唐高僧玄奘、大唐和尚慧超与东晋高僧法显经行帕米尔高原纪念碑。纪念碑背面的远处,亦即走廊进口的两边,一侧是肉眼可见的皮斯岭达坂,以及达坂上只要运用望远镜方可分辩的千年戍堡,另一侧则是喀喇昆仑北端那个颇有名望的红其拉甫达坂。这片深远而又广阔的视界,将人带入一个陈旧的、长远的时空。在这幻影般的时空中,一队队的军旅、一队队的商贾、一批批的僧侣,一个个的探险家,风餐露宿,简衣陋食,鞍上马下,十去七归,却如缕不绝地行走在这条横贯亚洲天界的羊肠小道上,以路笔心墨,书写着一部跨过数十个世纪的前史长卷。
生命的边沿地带
瓦罕走廊我国段进口狭隘,入内后却顿感开阔,好像一个曲颈瓶,喉狭而内阔。沿喀拉其库尔河(又叫明铁盖河)西行不久,就有岗兵和红白相间的横栏拦截在路面上。严厉的验证作业耽误了一点时刻,直到经过电话向县政府核实,才开栏放行。
走廊内的风光漫长而又单调。土褐色的山,托举着银白色的冰川。冰川融水沿着峻峭的山涧冲向河谷地带,然后是稀少的卵石、瘠薄的草滩、跳跃的旱獭与小群的红嘴山鸦,偶然还有鸲和鵖的身影在乱石间跃动。细长的喀拉其库尔河逶迤弯曲,将公路引向遥不行及的远方。印象中,虽然此地并非“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”,但稀少的生物种群与深远广阔的天然空间比较,却显得若隐若现,满目寂寥。其实,想想也是,海拔4000米以上,这本已是生命存在的边沿地带。不管生命多么坚强,也只能存在于地质空间所能给予的狭缝里。如此看来,瓦罕走廊的价值,恰在于人类从地质空间的否定中,建议并完成了自己的再否定。假如它恰巧是一处小桥流水、莺飞鱼跃、瓜豆桑榆、大路通衢的富庶之地,它还值得咱们如此搜肠刮肚地去唤醒前史的回忆吗?
作为这种前史回忆的地标之一,是那个坐落于喀拉其库尔河南岸的吐拉炮台。假如不是刘湘晨教师事前提示,咱们简直要在迂回弯曲的走廊中丢掉了它。它荫蔽在一段蛇形廊道后边的制高点上,这儿恰恰又是这段河谷的蜂腰地段,足见其作为一处军事筑垒在选址上的精明。炮台残迹六七米高,土石结构,北侧有阶梯通往顶部,东西两边设有简略的、现已崩塌的胸墙。从其结构以及现有的破损程度来看,它不是一座具有长远前史的建筑物,应归于近代所为。对此,直到捉笔行文时,尚不能查到前史材料,有说是建于民国时期。
吐拉炮台居于走廊东段的狭隘部位。这个狭隘部位的中心凸起,挺拔于喀拉其库尔河的南岸,与南北两翼的峻岭构成一个元宝形断面。站在这个方位,足可俯瞰并把守北侧的河滩与南侧的缓坡地带。其效果,无异于通道上的一道高效的闸口。但关于“炮台”这个称号,我有些犯疑。炮台本身的矮棱柱形状及其实心结构不足以工作一门炮,炮台周围只要粗陋的步卒胸墙,没有炮位,炮台所在的峡谷中也没有满足的弹道空间。这一切让我觉得,所谓炮台,很可能仅仅人们对这种边关戍堡的象征性的称号罢了。从准噶尔南缘到巴里坤草原,乃至北天山南坡的赛克散戈壁,我曾多次见到过这种因地制宜、因陋就简,却不乏前史意义的边关筑垒。
但不管吐拉炮台归于哪个前史时代,也不管它的战术功用怎么,它无疑归于这条陈旧通道数千年前史中的一个环链,一个梯级。它和朅盘陀国石头城、好日子嘎拉古驿站、皮斯岭公主堡等前史遗址相同,是帕米尔高原文明长卷中的一个故事、一段文字、一个符号,乃至仅仅一处存疑和空白,增添了这部前史长卷的本身价值。
疑似明铁盖
脱离吐拉炮台,沿喀拉其库尔河持续向西不久,就来到一处叫做明铁盖的当地。车子驶入了一段地形较高的“S”形坡道。我误以为咱们经过的那道“S”形坡道就是明铁盖达坂,因而心中生出很多疑问。明铁盖达坂曾是从印度次大陆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传统通道,曾与中亚山区的乌孜别里达坂、别迭里达坂齐名。仅仅因为近百年来冰川的腐蚀,难以通行。但眼前这段坡道,除了地形稍高之外,并无任何险恶之处。不光与一道冰雪达坂的应有态势相去甚远,乃至与我心目中的勾画也有大相径庭。但环顾四周,在这块标有明铁盖地名的当地邻近,好像也没有一处足可称为达坂的地貌。视界所见,只要一条模糊的路迹通往西南侧的万山丛中,令人发生模糊的遥想。
但越往西行,海拔高度越来越高,这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。从两河汇交点处的3600米到明铁盖路口,咱们现已上升了约300米。持续往西到科克吐鲁克,还要上升400米。这条通道一向延伸到阿富汗境内的海拔5000米以上区域,刚才呈现向西下降的趋势。那时,流动在走廊内的已不再是东去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喀拉其库尔河,而是西去汇入咸海的喷赤河了。
几天之后,当我在谷歌地球上去分辩那些似曾相识的遥感地貌时,总算能够断定,那座标高4703米的实在的明铁盖达坂,坐落那段坡道西南方向22公里的喀喇昆仑山中。而那天所见的“明铁盖”,只不过是通往明铁盖达坂的一个路口处的称号罢了。那里与明铁盖达坂的高差将近800米,也难怪找不到那种雪域边关的感觉。
马蹄形的山间草场
朝晨动身,咱们又向西驰行了大半天,半途只在喀拉其库尔河畔歇息了20分钟,啃了半块馕作为午饭。因而,抵达托克满苏时,世人已感劳顿。但咱们深知不是到这儿来做客的。方案中的行程只要两天,而可用的作业时刻却只要当天的傍晚前以及第二天的清晨。早餐今后,咱们就得起程赶回塔什库尔干,以便跟上整个团队的举动。因而,在咱们在达托克满苏了解到一些状况后,又从头起程,在满天阴云的笼罩下,去拜访涣散在沟沟壑壑中的牧群和牧民。
面临这个广大的马蹄形山沟,咱们不免有些忐忑。面前那个横栏在进口方位的兵营,明显宣示着这片土地的边关位置。
8月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,秋草现已开端疏落,加之从托克满苏到克克吐鲁克之间的地段,只要为数很少的小型牧群,咱们只好持续向西,终究把目光专心在瓦罕那片广大的马蹄形草场内。远远看去,这片区域内寓居有四五家牧民,散布在被两条山溪分割出的几小片台地上。他们的背面,就是挺拔的、多雪的兴都库什山。与兴都库什山那些巨大的山体比较,那些牧舍矮小得简直能够忽略不计,而活动的牧群简直能够与山坡上的乱石混为一体。但却正是因为它们这种循环往复的、无声无息的、但却是坚强的存在,至今还在维系着这条陈旧走廊的生命力。
这是一片坐落在帕米尔万山丛中的瘠薄的高原草场。进入8月,壮年男人连续转入东部的塔什库尔干河谷收割草秣,白叟、妇女和孩子们是这片草场的主角。傍晚前,他们带着那种仁慈的、羞涩的、憨厚的浅笑走出门扉迎候咱们。带着粗重的喘息,咱们络绎在草场上,用肢体言语与孩子逗弄,用手势言语与妇女和白叟扳话,用仅剩的膂力躲闪着牧羊狗、追逐着为数不多的牧群,用镜头凝结住他们的日子。那天下午,阴灰的云层一向驻留在天空中不愿散去。一般来说,这是一个不利于拍摄的气候。可是,已然高原人本来就是日子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气候中,咱们便也甘愿凝结住其本真,以便给它一种实在的解读。